今年4月11日,上海浦东机场,从印度尼西亚度假回国的徐某和吴某刚刚踏上国土,即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
这对“80后”夫妻曾经是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网店时代的弄潮儿,原来是“制假、售假大户”。他们通过网络制售假冒名牌化妆品,涉及品牌10余个、类别达300种之多,仅警方现场查获2万余件假冒国际品牌化妆品,涉案价值1000余万元。
他们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公开制假、售假?互联网如何成为制假、售假的主渠道?行政监管存在怎样的盲区?
徐某83年人,毕业于某名牌大学。大学期间,颇具经商头脑的他像许多大学生一样开始了“低成本创业实践”——购买网上所谓的“低价正品”化妆品进行校内销售,从中赚取差价。
2008年,徐某在网上注册了一家网店,打着“低价正品”的旗号进行假化妆品的网上销售。在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尝到甜头的徐某转而想自制化妆品,并于2010年6月,和妻子吴某在江苏苏州和上海徐泾各租赁一套别墅分别用以假化妆品灌装、存储销售。
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徐某的生意越来越好,月平均非法获利近30万元,还雇佣了一批临时工为其干活,其网店也成为某网购网站上知名的五皇冠店铺。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已然“成功人士”的徐某夫妻二人是值得学习的年轻创业“标兵”。
今年3月20日,接到举报信息的上海青浦分局经侦支队经过周密调查,锁定徐某位于上海青浦的售假窝点,当场查获了2万余件假冒国际名牌品牌化妆品,涉案价值1000余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万某等6人,而主犯徐某、吴某当时正在印度尼西亚逍遥旅游。通过进一步工作,两位犯罪嫌疑人终于4月11日被警方成功劝返。
据悉,徐某等人制售的假冒化妆品涉及品牌10余个、类别达300种之多,拘捕罪名包括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和涉嫌销售假冒产品。
在徐某的黑网店中有一款15ML的“雅诗兰黛”眼霜销量特别好,正品的专柜售价为200多元,徐某则打着“厂家处理”的标签把售价定在85元,而事实上,造假成本不到30元,盈利率近乎200%。
为了给商品的低价找一个托词,徐某在包装上贴着“限量版”、“试用装”、“小样”等标签。凭借这种低投入、高回报的产销模式,徐某夫妻赚得盆满钵满。
在位于苏州的加工点,徐某囤积着大量用于生产化妆品的灌装机和喷码机等设备,以及从苏州、广东等地购进的化妆品原料,以及大量名牌化妆品的空管、空瓶、包装盒。
化妆品属于人体皮肤直接接触类的产品,假化妆品往往制作含有各类廉价添加剂,其中铅和汞的含量往往较正品高出很多,经常使用会对人体造成损伤。
据了解,徐某“五皇冠”网店的好评率达到99.7%,买家则多来自二、三线城市,且热衷于购买“低价高档”化妆品。徐某在销售过程中充分利用买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积极“七天包换”、“不满意退货”等网购纠纷解决方案,既轻松赢得了店铺“声誉”,又巧妙地避免了黑色产业链的曝光。
商品条码在商品流通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可以标出物品的制造厂家、商品名称、生产日期等许多信息。在日常消费生活中,人们对商品包装上的商品条码也非常熟悉,甚至默认其为防伪标识。同时,随着扫描类移动APP(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发展,日益壮大的网购人群都习惯用手机“扫一扫”商品条码,以求购物安心。那么,这种随时随地的辨假方式真的靠谱吗?
为解开这一疑团,办案警方在记者面前任意取了一瓶某国际知名品牌粉水进行现场检验。警官通过手机上自带的APP进行扫描,结果显示,该产品信息与外包装信息一致,专柜均价为252元。但办案民警介绍,这只是在徐某作坊中缴获的一件假冒产品,在网上售价为120元,其成本却只是20元出头。
文章来源:人民网
华碧鉴定所可提供塑料、橡胶、纤维、涂料、胶黏剂等高分子材料相关鉴定服务,对各种材料及材料制品质量分析、成分分析、结构分析、化学性能分析、同类性和同一性方面做出准确物证鉴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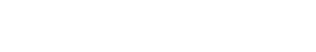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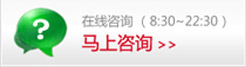
 立即咨询在线鉴定专家
立即咨询在线鉴定专家

